别具一格的唐诗读本,气象万千的浪漫初唐,《唐诗寒武纪》节选——
浪漫的初唐
别具一格的唐诗读本,气象万千的浪漫初唐,《唐诗寒武纪》节选——
浪漫的初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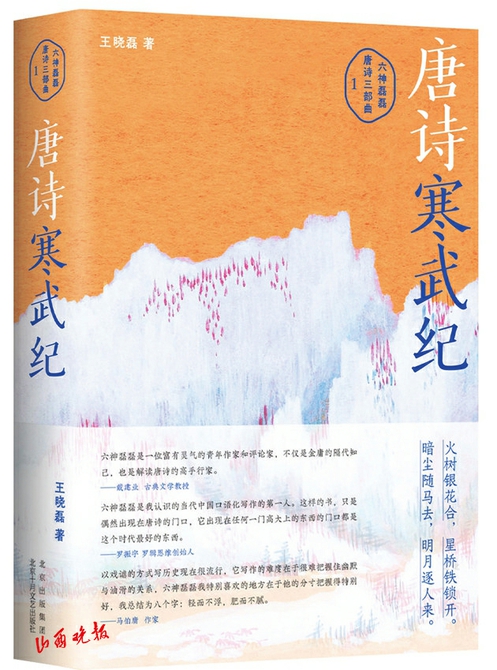
《唐诗寒武纪》王晓磊(六神磊磊)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该书是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的第一部。从六朝到初唐,从谢灵运走出乌衣巷、开始少年游的405年,到天才涌现、点亮星河的初唐之末,时间跨度三百多年。作者打通时光隧道,走进大唐的诗歌江湖,围绕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杜审言、上官婉儿、张若虚、陈子昂等的独特际遇,讲述了在诗歌高峰——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出现之前,诗坛怎样冲出沉闷乏味,就像生命在寒武纪爆发一样,气象焕然一新。
一
“初唐”时代结束、“盛唐”时代开启的时间,一般认为是705年。而恰恰就在这一年的元宵节,诞生了一首十分美丽的诗,叫作《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这首诗所写的,是东都洛阳的元宵之夜。
唐朝的大都市生活其实没有你想象的浪漫丰富,平时是要宵禁的。黄昏之后,“闭门鼓”咚咚打过,城中的里坊关闭,大门落锁,人就不能上街了,否则被禁军抓到就打屁股。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除外,不必宵禁,叫作“金吾不禁夜”。什么是金吾?就是打屁股的禁军。
一年只能嗨三晚,市民当然要抓紧机会狂欢了。于是乎到了晚上观灯之时,城里人山人海,一片银花火树。城河被映照得如同天上的星河,美丽的歌妓浓妆艳抹,踏着《梅花落》的歌声在人潮中穿行,处处流光溢彩,恍如天上人间。
然而有一次,我又无意翻到《正月十五夜》这首诗,忽然浮起一个念头——这首诗恰好诞生在初唐之末、盛唐之初的分水之年,岂不是很巧?
它所描写的固然是元宵美景,但如果我们用它来形容初唐的诗歌,不是也很恰当吗?
二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站在公元705年的节点上,回头望去,看视有唐以来九十年的诗,看它从最初的萎靡,到此刻的气象万千、火树银花,难免产生“星桥铁锁开”的感慨。
按理说,这铁锁,似乎开得晚了一点,诗的勃兴应该早些到来的。它的准备工作其实早已经就绪了。在唐朝建立大约四百年前,东汉末年的时候,五言诗就已经打磨成熟了。三国时代的人已经可以读到非常棒的五言诗。而在大约两百年前,到了南朝刘宋的时候,七言诗也已经准备就绪。那个时代的大诗人鲍照已经可以熟练地用七言诗高呼:“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
这时,诗的繁荣还差一块拼板,叫作声律。前文中我们已经讲过,同样是一句话,同样的字数,为什么有的读起来就声韵铿锵、悦耳动听,有的读起来就十分拗口?人们慢慢意识到:这是声律在暗中起作用。
在唐朝诞生之前一个世纪,这最后一块拼板也终于被补全了——有一个叫沈约的聪明人,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了一套关于诗歌声韵的规律、诀窍和禁忌,发明了“四声八病”之说,让一种全新的诗——律诗的诞生成为了可能。
此外,唐代诗歌中最重要的几种题材:边塞诗、怀古诗、离别诗、留别诗、闺怨诗、咏物诗、山水田园诗、酒后撒疯说胡话诗……都已经齐备。每一种题材都已有杰出的前辈写过,留下了许多模子和范本。
关于诗的一切关键要素,到隋唐之前都已经完成,就好像柴薪已经堆满,空气已然炽热,就等待那最后的一丝火星了。可它却迟迟没有出现。
沉闷、燥热、无聊……人们熬过了唐朝最 开始的数十年,情况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火种依旧在深处封存着。
那些年里,撑持着诗坛台面的,是一帮宫廷里的老人。他们从旧时代走过来,身份高贵,谙熟经典,训练有素,出口成章,但却又是那么缺乏创造力。他们也不满意现状,想要改革,想要振奋,不愿再像前辈那么绮丽、琐碎和柔靡,但他们却又看不到前路,走不出过去的泥淖,只好狐疑地把宫体诗一首首作下去。
今天的许多唐诗选本,第一首都放王绩,那是没有办法,不是王绩同学非要抢沙发,而是他的“长歌怀采薇”,实在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清新的句子。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人们猛一回头,才发现亮光已经在不经意处出现了。一批小人物昂然举起了火炬。
跟着我们来!他们吼道。诗,打从一开始“三百篇”的时候起,就不只是宫廷里的玩物啊。谁说只有达官显贵才可以写呢?
我们小人物也可以写的!谁说只有吃饭喝酒、观花赏月才能入诗呢?我们还要写江山和塞漠。
人们观望着、犹豫着,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到了他们身后,那火把汇成一条长龙,大家呐喊着,向八世纪浩荡进发。三
今天,许多学者都对唐诗的这一个时期很感兴趣,他们像做生物研究一样,取下这个时期的一些切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
有一个日本学者叫作松原朗,专门研究了这个时期的一样东西,叫作“宴序”。
所谓“宴序”,就是当时文人们搞派对时所作的风雅序言。它可不是今天宴会的菜单、礼单之类的俗物,而是很有信息量的,能反映出文人活动的情况,比如一次派对有多少人参加,会上大家写了多少诗,等等。
松原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到了“初唐四杰”的时候,宴序的数量猛然增多了。也就是说,大家喝酒、作诗的活动开始频繁了。
“四杰”流传到今天的宴序,多达五十四篇。相比之下,之前吴、晋、宋、齐、梁、陈整个六朝几百年里,留下来的宴序总和也不过只有七篇。而在“四杰”之前的唐初五十年,则一篇宴序都没有。
他认为这侧面说明了一件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诗。
人们开始不仅仅在长安、在洛阳写诗,也在各个州府县城、馆驿茅屋、水畔林间写诗了。
他们之中,许多是中下层的官僚,甚至寒门士人。他们没有资格写宫体诗,于是更多地描绘各色江山风物、社会人生,更自由地抒写心情。
江湖翻腾起来,新的风格恣意生长,诗坛不再千人一面,而是像物种大爆发般,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面对深秋寥落的山景,那个叫王勃的山西诗人,用一种庄严典雅的风格,写出了帅得人眼晕的诗句: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他抛弃了那些陈腐的套路,没有写宫体诗中“哎呀我真不舍得离开”之类的矫情句子,而是选择了一帧胶片感十足的画面——“山山黄叶飞”,作为诗的结尾。
面对月色下浩荡奔流的春江,一个叫张若虚的扬州诗人也果断抛弃了靡艳的辞藻,拒绝去雕琢琐碎小景,而是四十五度角仰望夜空,用空净华美的语言,直接叩问生命和宇宙的奥秘: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他的这一篇作品,就是后来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
随着“星桥铁锁开”,诗歌的世界终于“暗尘随马去”了。这暗尘,是沉积板结了百年的尘土,隋文帝发文件扫除不清,李世民亲自带头写作也扫除不清的,眼下终于松动了、拂去了,直到从四川射洪冲出来陈子昂,给了这“暗尘”以最后的一次涤荡。
于是“明月逐人来”,夜空一片开阔。不断有天才满溢的玩家加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他们竞芳斗艳、自在欢唱,完全不必担心它会太早结束,因为“金吾不禁夜”,这一场诗的盛世才刚开始呢!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