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秋夜》中的记忆叙事
《故乡的秋夜》中的记忆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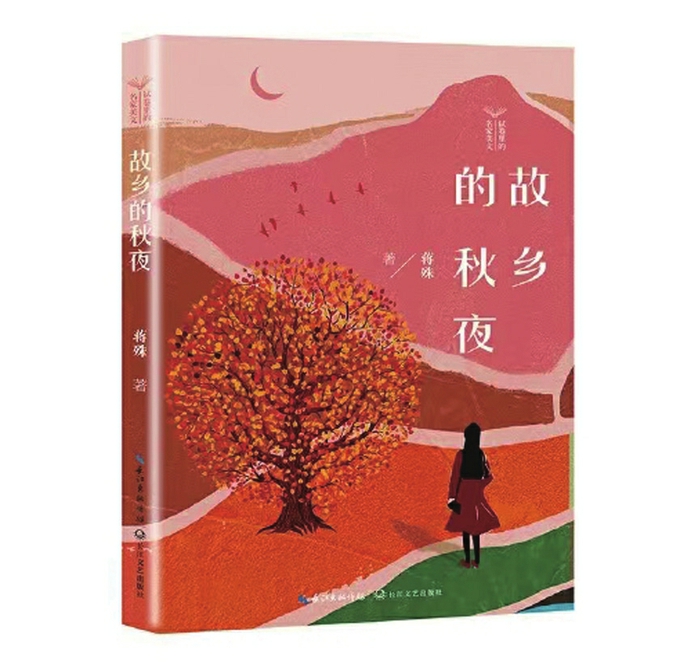
翻开《故乡的秋夜》,我窥见了作家蒋殊生命中隐秘的一角——记忆。记忆是一个人最为隐私也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正是因为那些生命中快乐的、忧伤的、愤怒的、个人的、民族的回忆,才构成了一个真正存在而又完整的人,而《故乡的秋夜》正是这样一部将记忆凝结成琥珀的作品。它以个体生命的悲欢为经,以故土风物为纬,以民族往事为骨,让那些闪烁的瞬间在文字中获得永恒的生命。
个体记忆是书中最为温柔的底色,通过文字感受的是蒋殊对亲人的爱、对故土的爱。爱让记忆珍贵,也为记忆构建起抵抗遗忘洪流的堡垒。这些记忆来自《我们在一起,多好》中对父亲的酸涩感情:是儿时盼望父亲回家的“我”,是被退学后满是眼泪的“我”,是在父亲写下“我们在一起,多好”7个字后内心泪如雨下的“我”;来自《我在不远处》中“偷窥”父母双亡的琴琴早早挑起生活重担,感叹少女的坚韧与倔强,同情其生活的艰难;来自《盛大的告别》里对亲友相继离世锥心刺骨的痛,以及对生命的反复叩问……这些文字并非单纯记录,而是将流逝岁月中的情感结晶成永恒。同时,蒋殊的个人记忆并非是刻意追溯的结果,而是像《阳光下的蜀葵》中描述的那样:当作者在朋友的微博中偶然得知,儿时故乡墙角那丛热烈绽放的野花学名“蜀葵”时,那些被时间磨洗得模糊的记忆如同《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我”品尝到小玛德莱娜点心时突然变得清晰——带着露水的花瓣、孩童的游戏、故乡的童年,所有被遗忘的细节顺着花名的线索汹涌而来。尽管再次回到故乡后院中已没有了蜀葵的痕迹,但蜀葵鲜活地停留在记忆里,承载着作家对故乡的爱与追忆。正如普鲁斯特所指出的,时间的线性流逝总会消解存在,而这些富有意义的时刻及个体对其的体验与感知,才构成了人生的全部意义。
个体记忆与故土风物、人文传统相交融,升华为更加广阔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不仅代表着个体的悲欢,更承载着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血脉。书中《翻山越岭去拜年》描写的是童年伴着星光便要翻山越岭去老舅家拜年的经历,《犹记兴家机杼声》中康秉文将声声机杼带入内蒙古……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旧时的文化已经慢慢被“淘汰”,但这些文化还保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中,作家通过文字将故事与记忆具象化为实在的物与事,使这些儿时独有的感受,扩展到有温度的集体记忆。
抗战老兵的故事构成了散文集中最厚重的记忆维度,这些老兵的英雄事迹不再是一串功勋文字,战争的悲剧也不再是一串抽象的数字,而是表现为一段人物故事、一首歌抑或是一封信。作者将英雄回忆以微小之物具象化,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沉重记忆也因此有了载体。当《心中军歌依然嘹亮》中的百岁老兵李月胜像孩子一般追问“为什么不让我去天安门广场”时,当《握在手里的荣光》中94岁的郝照余捧着给大哥颁发的烈士证双泪长流时,革命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时间线,英雄的功勋也不再是一个数字加一个数字,而是个体与个体的叠加。
合上《故乡的秋夜》,那些具体的记忆碎片依然在眼前闪烁:故乡的蜀葵、房顶的瓦楞花、抗战老兵的旧照片……蒋殊的《故乡的秋夜》既是个体的记忆、也是文化的记忆,更是民族的记忆。当记忆有了载体,文化有了温度,英雄不再被宏大叙事束之高阁,因时间带来的遗忘与对意义的消解便不攻自破。
焦一睿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