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的魔法
——读舒吾小说集《微风吹起黑色帷幕》
镜子的魔法
——读舒吾小说集《微风吹起黑色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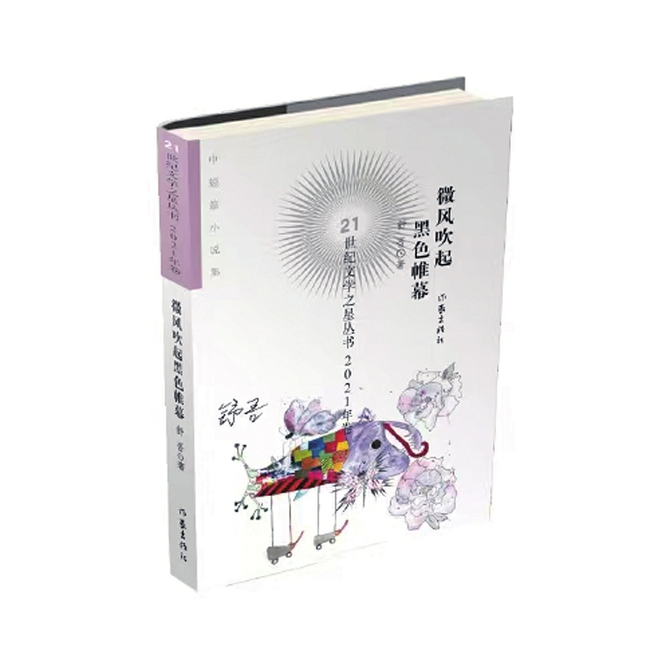
舒吾小说集中的《微风吹起黑色帷幕》《永远正确的人》《斑鸠之死》,以及《流放地》《飞鸟出现的时间》,一篇篇小说仿佛展开了一个个让人颇感新鲜的世界,吸引着人们去认识世间不同的生活样态,而且这些小说像是站立成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人物的内心,让人从中看到生活的某些真相。
我们眼前的舒吾,在小城度过了独属于自己的童年、少年。小城这个“万花筒”里蕴藏着各种源泉,其中一个源泉便是不完整性。她认为,那些被人们损坏或废弃的东西才是真的好玩,家里的小布头、核桃壳,或是一小片打碎的镜子,放在一起重新拼接起来,恰恰会成为一种新的形象。这种不完整,预示着与平凡生活的距离感或者间离性。它们被忽视、被抛弃,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或许这些只是早年生活的零碎印象,不料,她长大之后才发现,生活中真正完整的东西原来是如此之少,“我们所能看见的几乎每一面镜子都是破碎的,这样破碎的东西常常让我觉得心痛,但它俯拾皆是。这些碎片后来成为我写作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换言之,它还有另外一个不太确切的名字,叫做经验”。
这就触及了文学的本质性问题——经验乃人生之体验,没有体验就没有经验,对于舒吾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来讲,完整、总体、全面,一定是要有待于将来的,她在不断建构着自己,正如现实不断自我建构着由零碎到完整的世界一样。对于当下的写作者而言,舒吾有理由尽可能利用儿时的记忆,即早年生活的零碎印象来进行,“将这些碎片以一种颇有用意的方式组合起来,渴求它变成我所期望的、能打动别人的形状”。可见,她同样在纸上也重建了一个人间万花筒,诸般联系起来,便是松弛的、流畅的、有意味的,既体现了作者对文字法度的敬畏,又带有初出茅庐者的些许锐气。这种气度,一部分得自天性,一部分来自领悟力。而天赋与悟性,则成为一个致力于创作的年轻人的必备素质。对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写作者而言,观察力、经验和文字感觉,似乎缺一不可。
舒吾这一代人已经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即时通信工具,人们的互动方式,与他人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创作,她创作《斑驳的眼》便得自互联网引发的一些事件。当科技的后果让人警觉,人被迫与现实疏离,我们还能建构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的建构还会有深刻的意义吗?舒吾的小说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生活本身也在教育着人们,完善着写作者的纸上建构。
生活中的细节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有时候可能远超出完整的虚构故事。比如《你不应如此颤抖》这篇小说中,文学描写互证着现实,生活支离破碎,完整需要文学重建,但完整又是不可靠的,片段也好,细节也罢,有待小说艺术加以自洽:“一面完整的镜子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同样,随意排列的镜子碎片也是一样。”文学就是要知不可为而为之,试图重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自我是舒吾小说的另外一个关键词,现实中的我,他人眼中的我,镜子里的我,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被纠正、定型或刻板化的?她发现:“镜中的形象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化,抑或被扭曲,但大致的形象是真实的。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由此,舒吾将小说理解为一种纸上的装置艺术,是幻象,是再造的我们内心,不只是我们自己,我更想理解为拼接之后对现实的升华。
未知也可以构成对舒吾的概括。我们的所知诚然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未知”,每一次设想都通向未知,导致不同的历险,不同的历险则开拓着不同的可能。比如《酸鱼》这个小说中的米米、张磊和“我”,原来“在彼此眼里都是不可探寻的未知,他们无法从对方的行为判断对方的想法。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私下过着秘密的生活,怀揣着隐秘的思想,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呈现在其他人的面前,换句话来讲,我们永远也无法体察一个人真正的幸福与悲哀,我们最真实的喜悦与痛苦永远也不能被他人得知。”
好在探索未知正是文学的使命,有幸成为写作者,就是要用文学这种方式,去探索、去发现,去发问、去质疑,有时候未知不但能将人与人用一种奇妙的方式连接起来,同时,未知也像是一个试金石,检验我们作家到底有怎样的发现能力,并且能够经由怎样的方式,去铺就通往社会或自然界未知事物的路径。现在文学越来越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文学的使命,在于以自己的方式揭开未知的谜底,正如舒吾所说,人心之间永远横亘着的那一条“无法逾越的陌生河流”,正是文学探险的领地。
梁鸿鹰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