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节选——
《墨经》与先秦名学
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节选——
《墨经》与先秦名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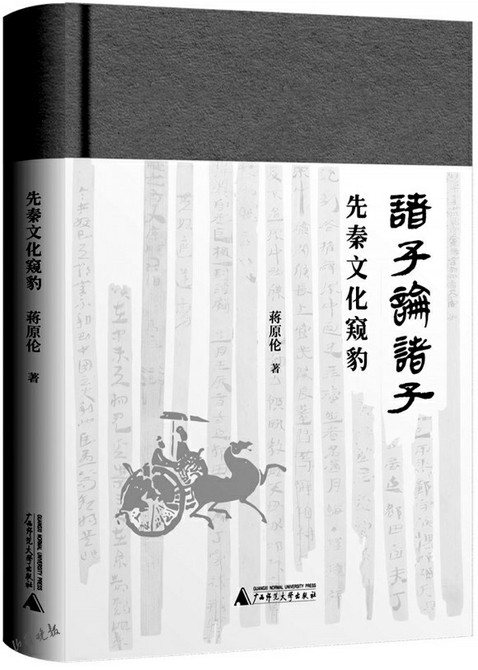
《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 蒋原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视角独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思想的更深刻理解。作者以对文本的敏锐洞察力,立足于墨子批儒、庄子鉴孔,韩非解老等论辩与攻讦,指出鲜为人知的有趣现象并给出独到见解,如孔子地位及形象在道家文本中演变背后的儒道争锋、韩非对老子思想的全面阐发和刻薄寡恩化运用。书中呈现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展现先秦思想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
据说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到过中国,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不爱做实验。这类笼而统之的评价虽然未见确切,但是大差不差。以儒家理念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似乎缺的就是这两大方面。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墨家就是这一例外。要说墨家非儒,以今天的眼光看,恰恰是在爱动手实验与数学、形式逻辑等方面的探究上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其他诸子,就这一方面来说,墨家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异数。
如果说古代中国尚有一些数学著作,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也陆陆续续有科技观察和科技实验方面的记录和相应的著述《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那么,逻辑学著作似绝无仅有,这就是《墨经》。所谓《墨经》,是《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的合称(后人又加上《大取》《小取》,共六篇),其内容丰富而庞杂,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等多个领域。西晋人鲁胜将此从《墨子》书中抽取,称之为《辩经》,其重点在于突出其逻辑学的内容。故在《墨辩注叙》文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这里,所谓“以立名本”,就是开创了名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逻辑学。
笔者揣测,可能是为了回应西方有关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说法,胡适早年的博士论文的功夫就下在《先秦名学史》上,这部名学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史。该著述的重点就是告诉读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先贤已经就知识的来源,判断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逻辑学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自觉的表达。在这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将惠施和公孙龙归在“别墨”一派中(此乃胡适概念上的误用,“别墨”是墨家内部各派之间以自己为正宗,对其他派别的蔑称)。之所以将惠施、公孙龙等归在墨派,是因为公孙龙等所讨论的问题,如白马论和坚白论在《墨辩》中均有提及和得到关注,可谓一脉相承。不过胡适认为《墨辩》诸篇章肯定不是墨子本人所著,因为墨子不太可能既是逻辑学方面最初的发蒙者,同时又是逻辑体系的创始人,并进一步认为《墨辩》诸篇即使不是惠施和公孙龙等所著,也应该是惠施和公孙龙那个时代的作品。
有研究者认为,在《墨辩》诸篇中,作者提出了“名”“辞”“说”等称谓,它们相当于现今逻辑学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三种形式范畴。这略有附会,细究起来,只有“名”相当于现今的“概念”,其他的逻辑学范畴在《墨辩》中并没有很对应的词,亦即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像今天的逻辑学教材那般一一对应。“辩”“辞”“说”“故”(前提)、“类推”(推理)等都反映了那时的逻辑学思想。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还把《小取》中提及的“或”“假”“效”“辟”“侔”“援”“推”,称为“辩的七法”。前两者“或”“假”是“立辞的方法”,“效”是演绎法,“辟”“侔”“援”“推”,都可以叫作“归纳的论辩”。所谓辩就是分辨、判断和区分的意思:“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墨子·小取》)
逻辑学往往是在辨析和辩论中产生的,惠施与庄子辩,公孙龙则通过自辩揭示了逻辑思维上的某些规律。使公孙龙声名大著的是“白马非马”论。不知为何,一直到现今,还有些学者称“白马非马”论为诡辩,公孙龙只不过是说“白马”的概念不同于“马”的概念,有错吗?没错!有一个故事说,公孙龙骑马出关,有关守接到上峰命令,不让马匹出关,于是公孙龙通过一番辩论,说自己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结果就顺利过关。这样一来,一个逻辑命题变成了一则公孙龙如何善于狡辩,以达成自己目的的故事。其实白马非马只是纯粹的逻辑学探讨,只涉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不是将白马看成一匹马的问题。
非常可惜的是,由《墨辩》和公孙龙等开启的形式逻辑和语言学话题,基本就到此为止,后世的学者并没有大的推进。虽然逻辑问题最初可能来自经验,但是由日常经验所造成的困惑一旦获得解决,那么对于超于经验的思辨,许多学派均不感兴趣。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言:“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了解)其意。”人们更倾向于把思辨方面的困惑搁置起来。所以,胡适说墨翟及其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也就是说,不排除有个别智者(如鲁胜等)对于形式逻辑问题有关注,但是像战国时期集中探讨数学和形式逻辑问题的学术团体,在两千年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形式逻辑面前,儒家倡导的礼是没有地位的,因为礼法包含着社会传统和具体的生活内容,而在形式逻辑中,这些具体的内容被抽取了。双方意见相左时,在辩论中决定胜负的是逻辑力量,而在礼法中,决定胜负的是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纯粹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辩论就被挤出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
其时,儒家奉《诗》《书》《礼》《易》《乐》为经典,墨家子弟则“俱颂墨经”(《庄子·天下》篇),这就显示出其不同于儒家和其他各家的品行。前文说了,《墨经》不光探讨逻辑学,它也是当时各科知识的教科书。《墨经》中有丰富的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有杠杆原理,有针孔成像,有几何学知识,等等。也就是说墨家子弟聚拢在一起,并不是念叨“兼爱”“非攻”这些信条,而是诵习墨经,学习科技知识,以运用到生产实践之中。尽管儒家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是真正践行“格物”的是墨家。墨家的强项正是儒家的弱项。儒家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仅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也表明社会的主流文化轻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果说诸子百家中,别的学派是以观念认识的标新立异非儒,那么墨家则是以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而非儒。
当然,这里似乎有些悖反,墨家是最注重生计实用的学派,因此《墨经》中包含大量的科技生产知识,但是为何《墨经》也关注形式逻辑这类丝毫没有生计实用价值的知识?其实,科技知识的进展必然依赖背后的逻辑思维。从墨家到名家,是思维拓展的必由路径。可惜墨家在近两千年的时光中一直被封存冷藏,直到清代,才为有识有志之士所发现,经毕沅、王念孙、汪中、孙诒让等一番校勘、注释、间诂,才重新见光。20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遂大兴。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