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水春汛:一卷流动的乡土诗笺
野水春汛:一卷流动的乡土诗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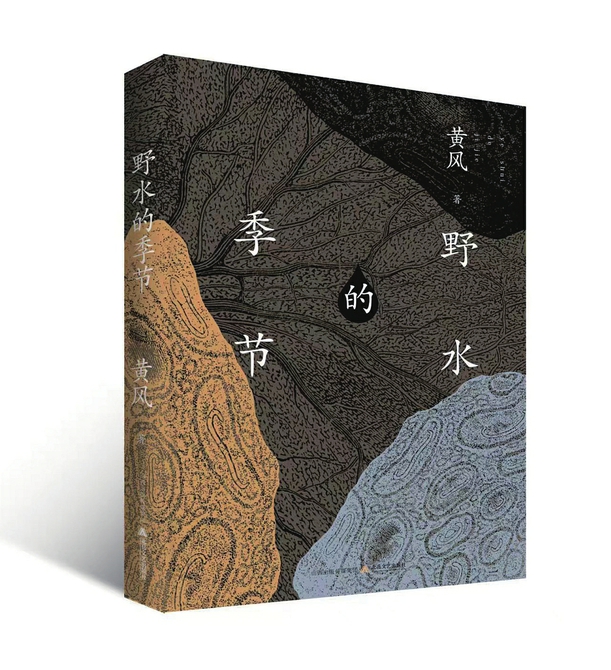
编者按
黄风是我省重要的散文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近几年他的散文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国内引起关注。
2023年底,他的散文《野水的季节》获得第十届冰心散文“单篇作品奖”。《野水的季节》首发于《山西文学》2022年第10期,先后被《散文选刊》2023年第1期、《海外文摘》2023年第2期选载,同时入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2022年度散文50篇》、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22中国年度散文》。
今年5月,收入该篇作品的散文集《野水的季节》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童年回溯”与“远足行吟”双线交织,收录了黄风近年创作的散文精品。上辑以诗性的笔触复刻乡土童年,下辑以文化观察者的视角漫游大地人间,构建出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
该书集个体记忆、文化寻踪与生态觉醒于一体,既延续了汉语散文的审美传统,叙事打破常规视角,童年书写摒弃怀旧滥觞,纪行散文跳脱猎奇窠臼,在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交界处开掘新意;又始终贯穿生态哲思,烟火人间被赋予生命共同体的隐喻,乃生态文学创作的范本。
本期选编3篇书评,从不同角度评析推介《野水的季节》,希望读者们喜欢。
这部以“野水”为名的作品,恰似一道生命之流——它以草木根系般的细腻笔触描摹雁北荒原的风涛与光影,又以野水奔涌般的跳跃想象力,在残雪寻雁的现实与儿歌碎片间切换,让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生态脱节与传统记忆在蒙太奇式的拼贴中显影。
黄风笔下自然物的力量,来源于对自然物象的细腻感官书写。风被赋予野性的生命特质:“风掠过屋脊,扒在烟囱口上,又似猫叫般呜咽了整夜”,“窜”“扒”等动作与“猫号”的声响交织,唤醒读者对料峭春寒的体感。这种拟人化并非表面修辞,而是构建了“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断枝“发出嘎巴巴如骨折般的声响”,老瓦“直立着纵身跃到台阶下”,阳光“如树木般丰茂生长,化作参天巨木”。自然不再是背景,而成为具有主体意志的行动者。作者以孩童般的惊奇目光与农人的经验视角,将自然的声响、气味、光影编织成稠密的感官网络,让雁北荒原的粗粝与生机得以纤毫毕现地展现。
作者采用蒙太奇式的拼贴,在《野水的季节》中:狗在雁门关的残雪里徒劳搜寻雁影,意识的镜头忽而切入飘荡的儿歌:“二月二,剜小蒜,狼一半,狗一半”,旋即闪回生小子们剜蒜的田野。在碎片拼接中,发酵出季节嬗变的迷离光影。《墙头上跑马》将此技法推向极致:孩童骑墙的视角如飞鸟般自由起落——俯视果园“花姐一拨接一拨”,平视田野“挣脱犁具的驴在撒野”,又跃上老爷庙屋脊“越过大湖般的田野瞭到远山”。空间在俯仰间无限延展,时间则如“飘着的雁叫声”悬浮不定,乡土经验在意识的经纬中获得了超现实的密度与诗意。
贯穿全书的“静观”美学态度,体现在对乡土世界的凝视中。无论是土地公在苹果园“呼噜噜抽水烟”的奇幻想象,还是老井在白气缭绕中被推土机“活埋”的平静叙述,作者始终保持着有距离的观照——不沉溺于情感宣泄,也不做价值评判,却饱含深沉的悲悯。这种静观既见于扇车手“操控扇车时对风力的精准把握”,也见于农人碾场时“一圈圈将谷物碾平”的耐心重复。它是对农耕文明的深情触摸,亦是对其必然消逝的无声哀悼。
在机械轰鸣碾碎乡土的时代,《野水的季节》以感官的精微与静观的智慧,为消逝的农耕文明立此存照。这部作品最终突破了地域书写的局限,在“野水的倒影”中照见的,不仅是晋西北大地的风土人情,更是所有正在消逝的乡土文明共同的生命回忆——那些被推土机活埋的老井、被纸片般撕碎的果园,何尝不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遗失的精神原乡?当我们在黄风克制的笔锋下触摸到“万物有灵”的宇宙观,触摸到农耕文明中“一圈圈碾平谷物”的耐心哲学,这部散文集便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一面照见生命来路与归途的明镜,让我们在野水的季节里,听见乡土灵魂在时光深处的低吟与回响。
张志婷
这个时代最清澈的回响
《野水的季节》如一泓未被现代性过度侵扰的野水,平静地映照着天空与大地。作品以双线叙事织就记忆与行旅的经纬,上辑回溯乡土童年,下辑漫游异域山河,却在“生态觉醒”的统摄下超越了简单的怀旧与猎奇,构建出个体生命经验与广袤生命共同体共振的深邃场域。
黄风的童年书写绝非沉湎于温情主义的怀旧滥觞,他以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冷静与虔敬,将“野水的季节”“八月的禾场”“墙头上跑马”等乡土记忆从个人情感中剥离,使之成为一方生态微缩景观的活态标本。作者摒弃了居高临下的抒情和议论姿态,让孩童的懵懂目光成为最澄澈的透镜,捕捉着乡土生命之间复杂而精密的依存关系。
当笔锋转向行旅见闻,黄风的文化观察者身份便凸显出非凡的锐利。“湄公河访礁”“石鼓隆隆”“我的汉阳‘往事’”等篇目,彰显了他拒绝异域风情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自觉。其目光穿透风景的表层,在历史褶皱与当代生活的叠印处驻足。他笔下的山川河流、古树飞鸟,不再是静默的风景或猎奇的对象,而是携带着历史密码与文明讯息的生动主体。这种对“异域”的书写,本质上是另一种更为辽阔的“归乡”——是黄风对人类文明根系在广袤大地中如何伸展、变异与存续的执着叩问和记录。黄风在“折一朵紫薇献给朱鹮”的虔敬姿态里,在“对一棵古榔榆的重构”中,完成了对“他者”生命尊严的庄严确认,消解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惯常的二元对立呈现。
整部《野水的季节》最为核心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用“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生态哲思的生命共同体隐喻。无论是对河畔追逐无形春风的野犬的凝望,还是对古榔榆年轮深处时间的倾听,黄风的文字始终涌动着一种万物有灵且彼此通感的深沉意识。在黄风的笔下,烟火人间不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而成为无数生命共享的栖息之所。作者童年记忆里的一草一木,行旅途中的一山一水,皆被赋予了同等的叙事主权。这种对“生态位”的深刻体认与平等叙事,让童年回溯成为对生命原初共生状态的追溯,让远足行吟成为对更宏大生命网络的勘探与致敬。
黄风以语言为舟楫,在记忆的河流与地理的经纬中穿行,最终抵达的并非怀旧的彼岸或猎奇的异邦,而是一片万物互联、彼此映照的生命共感之地。《野水的季节》以其清醒的生态意识、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沉的生命共感,为中国当代生态散文探寻了更远的距离。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乡土是生命与生命相互确认的居所,真正的远行是向所有生命内在关联的回归。
当野水奔流,当季节轮转,它带走的不仅是时光的印记,更冲刷出了我们对生命共同体的重新认知——那是黄风以文字镌刻于这个时代最清澈的回响。
董啸
飞驰想象中的山野灵性
《野水的季节》以“野水”为名,既描摹了自然风物的本真样貌,也探讨了生态与自然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脱节与融合,是其书写生态文明生命力的鲜活注脚。
在想象的维度上,黄风的文字拓展了感知的疆域,以多元生命形态观照自然。其叙述视角富于变化:时而化身童稚的“你们”,时而转为怀恋故园苹果树的“我”,甚至幻化为神话之“年”或山林野水……无论视角如何流转,“在地性”始终是其文本的深层基质。通过野水的奔流、草木的气息与山峦的静穆,文本重构出一个充盈诗意与神性的自然世界,深刻寄寓着对生态伦理的深切呼唤。
《墙头上跑马》中的“你们”是摛开双臂、呼风唤雨的孩童,太阳、土地、村庄是“你们”的跑马场,冬夜里的风是猫、是狼,在呜咽与长啸中漏出天外的星光。喧闹声中,孩童们向老师求饶、摘榆钱吃“拨烂子”……喧闹声最终汇集为那个瞭望的背影,眺望村外的世界。这瞭望,并非寻常的驻足远观:它是一道由泥地里打滚的野性、墙头上腾跃的轻狂、被风霜打磨过的好奇共同熔铸而成的目光。几个小小的背影,稳稳地立在村口那截饱经风霜的老土墙上,仿佛不再是嬉闹的顽童,而是这片古老土地悄然竖起的、最年轻也最敏锐的触角。
散文中融入的魔幻元素,深化了文本植根乡土、表达多元的特质,展现了作家如何以想象穿透山林肌理,以物我交融的姿态书写万物灵性与奥妙。如《两页书》中,“我”目睹土地公与老井幻化人形,其妖异气息“宛若戏中悬梁起舞的白绫”。此处的“老井”,在缥缈烟雾中幻化为虔诚叩拜的妇人,又在时光侵蚀下显露满面伤痕、满身污渍的泥泞骷髅……此非故弄玄虚的怪谈,而是作家以惊心动魄的魔幻笔触,为行将消逝的“草木”与“岁月”谱写的“留痕”挽歌。
经由作家想象的赋形,“野水”超越了季节性河流的地理范畴,升华为山野自然灵性的具象呈现。它浸透泥土的野性,是汾河沿岸古老血脉在四季轮回中的不羁流淌与蛰伏,是黄土沟壑间倔强生存的草木,是季风掠过吕梁山脉时留下的原始气息——承载着一种未被规训、未被过度人化的自然原力。
李敬泽在《中国2022生态文学年选》序言中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简化为‘我’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收摄于‘内面’,实则遮蔽了其作为‘大他者’、生存条件与实践对象的浩瀚意义。”黄风的写作正契合这种“去人类中心化”视角,致力于生态平衡的表述。《野水的季节》超越了地域风物志的层面:野水的涨落,成为大地生命力搏动的象征。黄风以深沉诗性的笔触,完成了一次对山野自然的“复魅”——引领读者重新感知土地的呼吸、河水的意志与草木的灵性,在生态危机的阴霾中,点燃了重建生命共同体和谐的希望之火,亦是对人与自然“诗意栖居”的回溯与践行。
薛景晗
相关链接
黄风,现居太原,山西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毕业歌》,散文集《走向天堂的父亲》《野水的季节》《被我的叫卖声感动的夏天》,长篇纪实《静乐阳光》《黄河岸边的歌王》《滇缅之列》《大湄公河》等。作品多次被国内外报刊、年选转(选)载并获奖。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