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原文明与世界互动视角下的中华大历史,《世界之中》节选——
“脱钩”与帝国的衰落
讲述中原文明与世界互动视角下的中华大历史,《世界之中》节选——
“脱钩”与帝国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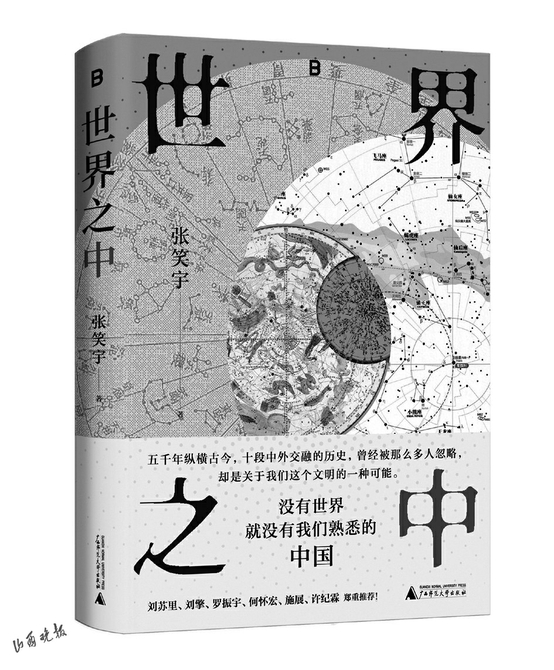
《世界之中》张笑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清末,本书摘取了十个鲜为人知又影响深远的历史片段,希望向读者呈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本书视野宏大,视角独特,观点精奇,论述得当,并将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等众多理论融会贯通,纵横上下五千年,为我们展示了许多曾被忽略又不得不叹为观止的历史画面。
张居正能够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乃至于大明王朝后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其实都跟两件事有关:第一,大航海时代的展开,明朝社会加入世界贸易大循环;第二,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是,全球化让世界变得如连通器一般:一处水位高则处处水位高,一处水位低则处处水位低。因为全球化繁荣而获得的收益,也会因为全球化的退潮而失去。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有几个处在全球化关键环节上的帝国都出现了各种政治危机。例如,在全球白银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卷入各种地缘政治冲突。比如,原属哈布斯堡王朝的荷兰地区因为信奉新教,与虔诚的天主教徒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发生冲突。当地起义不绝,导致腓力二世的军费激增。从1571年到1580年,尽管王室收入因为西属美洲的铸币税增长了一倍(以西班牙货币单位计,五年财政收入从390万杜卡特增加到800万杜卡特),但由于战争花钱太多,国王还是不得不于1575年宣布破产。
荷兰信奉新教,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宗教战争本来就是一场敌方不死不休的矛盾。要命的是,荷兰人“海上马车夫”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在那个年代,这批船上人在航海家、商人、海军和海盗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身份的,所以“海上马车夫”也有獠牙。自西班牙与荷兰开战以来,荷兰人就利用航海优势对西班牙的航路进行了封锁。其中对东亚白银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对两个港口的封锁:一个是果阿,一个是马六甲。这两个港口恰好一个通往印度,一个通往中国,都是当时劳动力最廉价、产品最丰富的地方,因而也是白银最大的流向地。尽管这些战场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文明中心,是毫无疑问的边缘地带,但是可不要小瞧这些航路贸易的重要性。当时东西洋之间贸易利润十分丰厚,到了一艘船的货物足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的程度。1628年,荷兰船长皮特·海因虏获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货物价值达到了惊人的1150万荷兰盾,五倍于卡特琳娜号的收获。此船的收入为荷兰军队提供了八个月的军费,让他们赢得了一场重要战争。
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不是唯一起火的地方,第二重打击来自日本幕府。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存在感其实很强,他们带来的白银和武器,引起了许多地方政权的兴趣,日本各地的大名也不例外。然而,当时日本主政的德川幕府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害怕大名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巨量的财富和兵力,挑战幕府霸权。因此,从17世纪开始,日本幕府开始以传教为由,限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与日本展开贸易,此即著名的“锁国政策”。“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整个东亚的白银贸易。
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还存在着第三重打击,也就是经济规律本身的涨消。我们前面介绍过,东亚白银贸易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白银短缺。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开采当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日本和欧洲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是做善事的,而是为了赚钱。在中国最缺乏白银的时代,最赚钱的生意还不是直接拿白银换瓷器和丝绸,而是直接拿白银换黄金。相对于白银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国保留的黄金相对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商人们把海外的白银运进中国,换成黄金,再到别的地方卖出去。
比如,隆庆二年(1568),中国的金银兑换比是1︰6,西班牙的金银兑换比则超过1︰12。也就是说,如果有办法从西班牙带白银到中国,换成黄金带回去,利润就能达到100%。但是,随着套利生意规模的扩大,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高银价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天启七年(1627)以后,中国的金银兑换比已经涨到1︰10到1︰13,而西班牙的比例则在1︰13到1︰15之间。套利空间缩小,白银流入中国的势头就衰减了。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规律的双重打击下,东亚白银贸易的规模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下跌。17世纪20年代,运往马尼拉的白银从23吨下降到18吨,到17世纪40年代则下降到10吨左右。
以上因素,使得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时代享受到的全球化红利不复存在了。大明王朝晚期,其金银兑换比上涨到了与西班牙接近的地步,这个数字不代表白银短缺得到了满足。因为白银循环的过程就像婚礼上的香槟塔一样,水必须先灌满上层的杯子,才会流向下层。
当外贸水流充足的时候,最先从外贸中挣到银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盗与外贸商,其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国内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银输入的政府机关,最后才是被减轻了束缚的老百姓。然而,当外贸的流水被从源头上关闭了,最先遭遇货币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崇祯十一年(1638),一千枚(一贯)铜钱能兑换0.9两银子,到清顺治三年(1646)就只能兑换0.17两了。
老百姓一银难求,然而一条鞭法的规定又是交税必须交白银。当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地给民众挖了坑。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一次没有位高者理顺治理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来给大明王朝续命了。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崇祯元年(1628),高迎祥反;三年(1630),张献忠反;四年(1631),李自成反。八年(1635),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过天星、九条龙等十三家首领会于荥阳,同年高迎祥攻破明中都凤阳。十四年(1641)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十七年(1644),张献忠破重庆、成都,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于景山。
辉煌灿烂的大明,号称全球“白银地窖”的大明,结局竟是如此惨淡。当然,白银循环连接的另外一个主角,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白银循环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收入下降。在16世纪的最后五年里,西班牙王室平均年收入2640万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缩到40万杜卡特,而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每年要花费400万左右杜卡特。腓力四世即位后,王室在1625年宣布破产,两年后再度宣布破产。到这时,很多银行家已经完全不想把钱借给日不落帝国的国王了。
财政破产的直接结果就是司机因为没油,已经开不动车了。不仅荷兰这台车出了问题,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这两台后花园里的车也熄火了。17世纪40年代,以上两个地区先后发生叛乱,而为了扑灭家门口的灾难,国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兰等其他交战国签订和约,八十年战争结束。战后,荷兰获得独立,瑞典获得大量赔偿金,法国获得大片领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满盘皆输,从兴盛走向衰落。
从17世纪全球化退潮的角度看,白银循环的衰落竟使东西方两大帝国同时崩溃,而这两大帝国的精英对此又全无认知。无怪乎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视野天生受到局限,不能跳出一国一社会之外,真正站在太空高度俯瞰地球,那么即便是再聪慧的头脑、再高级的政治家,所思所想也不过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真正直面一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那场“脱钩”,所有人都是无意为之,所有人都是无心受过。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