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田园
小说里的田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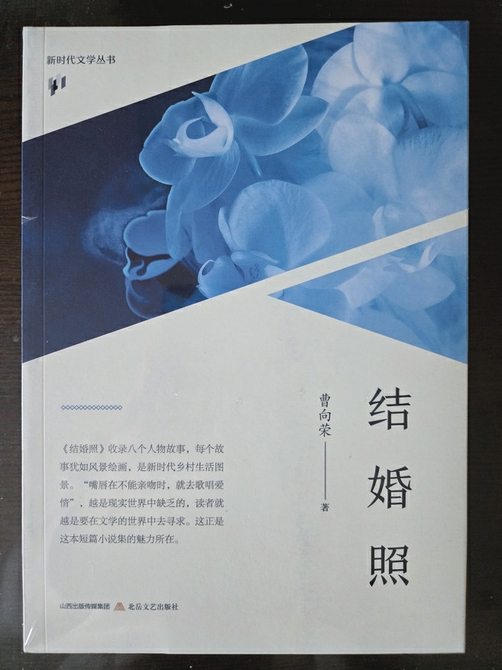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曹向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3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文艺报》《山西文学》《黄河》《小说选刊》等。2013年入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曾获2004-2006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泥哨》《打街》《夏夏的爱情》《结婚照》,散文集《消停的月儿》《木版年画》等多部作品。长篇小说《玉香》入选山西省百部长篇小说“布谷鸟”原创系列丛书,长篇小说《古渡》入选中国作协举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创作”活动的长篇小说改稿会,即将出版。
《结婚照》这本小说集收录了我2016年至2017年写作的六篇小说和早期发表的两篇小说。
小说的出版,有一个好处是将写过的小说重新看一遍。近来将收录的文字挨个儿看一遍,我为曾经写过的风景、对话、人物感到可喜。这本小说集里写两个光棍汉;写会画画的长富、唱样板戏的李老师、摇马车的臭臭;写有点赖的豁巴三宝、得不到命运眷顾的漏娃。少有人能活百年,小说里的人物或者能够长久地活下来,小说里的场景、时代的气息或者能够永存,这是件难得的事。我希望这本书里的文字,能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是本乡村系列短篇小说集,2016年12月写下开篇《光棍汉》,2017年连续写了五篇。写这几个短篇小说,我的劲儿很足,头脑里有多个人物,想着会写很多篇的,写得也还顺手,每开一个头,一篇就利落地写完了。《光棍汉》是这样,后来的这几篇也是这样。我将这些个短篇小说叫:田园小说。
从写作的时间上看,写这些小说,有那么点小小的急迫,一篇刚写完,下一篇就有了开头;前一篇初稿没完呢,下一篇的开头文字已经写下来。在此出版之际,回头看,觉着那两年真是写作短篇小说的好日子。
小说《光棍汉》是在我所写的小说里头较为喜爱的一个短篇,是用散文的笔漫画出的两个人物。一个家庭里,两个男人一块生活似乎没什么不对,却是各样的不和谐:兄弟两个像女人一样争长论短,亲人之间是那样生分。读这篇小说,仿佛看见屋顶被细风摇散的炊烟。《长富》发表后,我常常翻开重新看一遍。长富是个画匠,画炕围、画民间的绘画,皆带着古老传统的气息,犹如绝唱。《豁巴三宝》写一个喜剧化的人物,相信在生活中,人们都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两个。他对生活不认真,是人群中的懒者,受人白眼,成天被挖苦,但他不为所动,照着自己的意念一天天过日子。豁巴三宝也有积极勤快的时候,比如下井掏沙石。尽管下井是危险的。再比如,孩子们喜欢豁巴三宝。豁巴三宝能给孩子们快乐,能不理睬家长的埋怨教孩子们游泳。在孩子们眼里,豁巴三宝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小说的终了,豁巴三宝从洪水中去救人,因体力不支被洪流冲走了,就像生活中的小插曲,三宝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的一生。生活中,像豁巴三宝这样儿的人物,现在还有,他懒怠、逃避、饱受指责,但躲开他不见光的那一面,那深藏着的另一面却也是高大的、闪光的。
两篇早期发表的小说,一篇是《结婚照》,一篇是《泥哨》。
《结婚照》于2012年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傅书华老师这样评价:“《结婚照》故事很简单,刘勇、阿秀虽然结婚二十年,却没有正式的结婚证书,为补结婚证书而照结婚照,从而在补叙中写了二人的夫妻感情。小说以写阿秀的感觉为主,通过写阿秀的感觉,写出了现代社会所久违了的简单而又淳朴、清新、健康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小说全文的散文化抒情笔调,又强化了这种现代社会久违了的简单、淳朴、清新、健康的男女之情。如果说曹向荣这种在叙述中的抒情笔调对作品意义的呈现是‘龙’,那么,《结婚照》在作品中对结婚、对男女感情真义的揭示的象征意义,确有画龙点睛之妙。西谚云:嘴唇在不能亲吻时,就去歌唱爱情。越是现实世界中缺乏的,读者就越是要在文学的世界中去寻求。这正是曹向荣作品的魅力所在。”
《泥哨》写于2003年年末,发表于2004年,入选当年《小说选刊》第12期(下半月)首篇。我2002年开始写小说,在《泥哨》前只发表了《唐妮》和《打街》两个短篇。《泥哨》是第一个中篇小说。发表这个中篇小说那年,我三十五岁。这个小说开始写一个儿童玩具泥哨,写了一个年轻男人,又写了一个年轻姑娘。姑娘跟爷爷是一家人。年轻男人成了家,有了女人和孩子。就是这样,两家人因为泥哨相互走动,他们在风和日丽或者阴雨绵绵之时,演绎出人间悲喜交集的闹剧。后来出过几本书,《泥哨》这个中篇却始终不曾收录书中出版。在这一本乡村系列小说出版之际,我特别地将这一篇列在其中。我的写作,仅仅是为了热爱,它们是我生活的依赖,让我心生慰藉、让我感受到生活的踏实和美好。从这些文字里,我常常能触摸到生活的温暖。
我写这些,是念我的家园。那时候,七弯八绕的胡同,有扫帚清扫的印迹。干净的道路上行走着猪和羊,鸡成群地在地上啄食,狗轻轻地跑过去。一头牛靠墙根卧着,慢慢地咀嚼。墙角系着一匹马,发出吐吐吐的声音。一只猫,不知从哪里窜出,上了屋墙,从屋墙上走着,跳上房檐不见了。不知名的一只鸟悄然地飞落到墙头,东张西望。那时候,我眼里的人是年轻的、美貌的女人们,手把织物,成群坐在巷头的槐树下,悄声絮说或者大声谈笑。男人腰身强壮,一个人在挪动碌碡……
我写着记忆里不能忘却的人和事物,写我所热爱的家乡、热爱的土地,和亲切的人们。我的小说里也有很多的风物,比如,写家乡的土墙、写家乡的小庙。那时候,家乡的田野是葱绿的,那绿不只有庄稼,还有各样儿的树,那树是桃树杏树酸枣树石榴树。小孩子来到田间地头,看见西葫芦花、南瓜花,那花儿是精致的,清鲜、美丽。那时候,天是蓝的,云雪白雪白,到处都闻得到土腥味儿,用文学的词叫:泥土的芳香。小说里不只是人与物,还有那时候的人情事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淳朴,人与人交情深厚,一家盖房、全村帮忙,这家的房屋就像是全村人的事业,不去帮忙是丢人的事情。那时候,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现在,伴我成长的房屋长满蒿草,那曾经光洁的门扇窗棂剥落得让人心疼。那小胡同被新盖的高屋遮挡着,屋门前弯弯的道路被房屋堵截,那曾经洒满槐花的光洁道路上也落着尘土。田野里的绿,最多是庄稼的绿了。树只有道路两旁的杨柳。土屋土墙拆掉了,乡间剩得不多的土屋失了生机,在角落里畏缩着。
前些日子,去一个地方参观,看见一位师傅在塑像,那雕塑一大半用大片塑料布遮挡着。成品前的作物看上去乱乱的。我盯着雕塑家身旁那堆湿泥,伸手一挖,团在手里。那湿的泥握在手里是舒服的,整个人沉浸在润湿的气氛当中,连同心肺都觉得温润许多了。
写着这些,写作到夜深,我常常有这么一样感觉:写这些做什么呢?人或物,与一个人相依伴十年二十年,就像被吞下的饭食,在这个人身体里研磨消化,被吸纳被融入血液。其实,我写的这些小说是想还原我童年所经历的那温馨的年代。我的笔力是不够的,就算写出生动真切的画面,也只是在镜框里——再是生花的妙笔也写不出一个自然的田园。可是,我就这样一篇篇地写,像学画画,一遍又一遍,想尽力勾勒一幅让人难忘的画面。
写作是辛苦的,写作又有着无尽的快乐。我写这些的时候,心是沸腾的,笔下跳跃着心里眼里的人物,我快乐得像回到了年幼时的自己。
曹向荣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