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培育读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国】扎根泥土的文艺之光
【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培育读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国】扎根泥土的文艺之光

赵勇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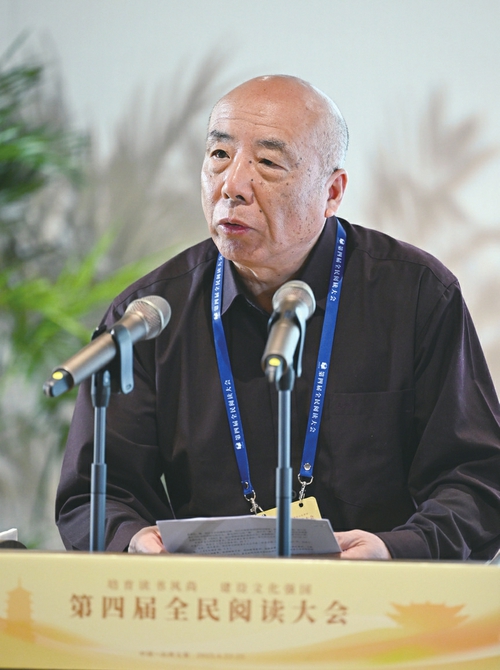
傅书华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葛水平 山西省文联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编者按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中,赵树理是一座丰碑。以他为领军人物的“山药蛋派”,用朴实无华的笔触勾勒出鲜活的乡村生活。那些从泥土里长出的故事,那些在语言中沉淀的智慧,正是中国当代乡土社会发展的精神体现。当我们再次凝望赵树理的身影,沿着他的足迹行走时,仍能强烈感受到其作品带来的震撼。4月25日至26日,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连续举办了三场“重读赵树理”系列文学讲座。赵勇、傅书华、葛水平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探讨了赵树理文学遗产的当代价值。今天,就让我们循着他们对创作风格与社会意义的精彩辑要,走进这位“人民作家”的人生道路与文学经典,感受他笔下直抵生活本质的大众化文学。
大众文艺的早期样式及当下启示
【主讲人:赵勇】
1930年左联成立,明确提出了“文艺大众化”是核心任务。1931年“大众化”被写入纲领性文件,这一举措为传统大众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瞿秋白是大众文艺理论体系化的关键人物,他主张大众文艺要为工农群众服务,用大众的语言写大众的生活,采用白话口语和方言,摒弃文言与僵化的新文学语言,并借鉴民间文艺形式,实现“旧瓶装新酒”。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的普及性和群众性,进一步强化了大众文艺,使其在延安时期蓬勃发展,成为主流文艺形式。正是在早期传统大众文艺发展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赵树理走上了大众文艺创作的道路,并进行了多方面颇为成功的实践,在多种文艺题材上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大众文艺的早期样式。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作品多为“问题小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如《小二黑结婚》聚焦自由恋爱问题。在形式上,赵树理大胆创新,采用现代评书体,将小说打造为“可说性文本”。他充分考虑到当时农村识字率低的现实情况,以农村识字人为桥梁,希望通过他们将作品传递给不识字的人。他的小说往往以说书人的口吻展开叙述。《登记》开头就极具代表性,从罗汉钱讲起,自然地引出张家庄张木匠一家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生动有趣,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传统的说书场景中。赵树理通过这种方式,让小说更易于被大众接受和理解,实现了文学与大众的紧密结合。
在曲艺创作上,赵树理同样成果丰硕。他创作的相声《很容易》、小调《王家坡》、鼓词《石不烂赶车》、快板《谷子好》等作品,丰富了大众文艺的形式。其中,鼓词《石不烂赶车》根据田间的民歌体叙事长诗《赶车传》改编。在改编过程中,赵树理运用自己对民间曲艺的深刻理解,对原诗进行了创新性改编。他保留了原诗的精髓,同时结合鼓词的特点,使作品更适合在民间传唱。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赵树理在曲艺创作方面的才华,也让普通百姓在欣赏曲艺的同时,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剧本创作也是赵树理大众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创作了《万象楼》《打倒汉奸》《两个世界》《十里店》等多部剧本,还创作了泽州秧歌《开渠》。他对上党梆子尤为热爱,为《三关排宴》编写的唱词,十字一句,一韵到底,为了这几句唱词,他花费四天时间推敲,展现出严谨的创作态度,也让传统戏剧焕发出新的活力。
赵树理在大众文艺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他出身农民又接受过教育,这种特殊身份使他成为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他在与农民和知识分子交流时,会根据对象调整表达方式。在写作中,他将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以通俗化的形式翻译、转述和改写给普通大众,让启蒙思想走进民间,他的作品成为连接知识分子思想与大众文化需求的桥梁。他那内容丰富而成效显著的大众文艺创作,也为我们当下文艺创作留下深刻的启示:
其一,坚守民间立场。赵树理自始至终扎根民间,民间立场是他创作的根基,而非后期刻意的选择。与众多作家不同,下乡于他而言并非获取创作素材的手段,而是全身心投入农村工作。在晋城下乡时,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的都是农村事务,诸如土地利用、种子选用、农田改造等,完全是一位实干的农村干部形象。他把为农民出谋划策、助力粮食增产视为比创作更重要的事。他在文艺创作中时时刻刻坚守民间立场,这种执着坚守,提醒当下文艺创作者要真正走进人民生活,关注人民需求,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温度的作品。
其二,偏爱民间传统。在赵树理眼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古代士大夫、五四以来文化界、民间这三个传统里,民间传统独具魅力。他对民间传统的偏爱近乎偏执,从他的各类创作中都能体现。以《白毛女》唱词为例,其质朴直白的民间唱词,农民一听就懂且十分喜爱。可要是改成古风或洋腔洋调,农民就毫无兴趣。这鲜明的对比,凸显出民间传统在文艺创作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下文艺创作应从中汲取经验,重视民间传统元素,将其融入作品,让作品更贴近大众,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避免过度西化或脱离群众的创作倾向。
其三,追求浅易文风。赵树理创作时把受众需求放在首位,为了让农民更好理解作品,在文风上煞费苦心。农民对“然而”感到陌生,他就换成“可是”;担心农民理解不了长句子,他便尽量写短。为了增加作品吸引力,他还会增添故事性,给人物起有趣的外号,像二诸葛、三仙姑等。他常用的白描手法,不仅遵从农民勤俭节约的习惯,还能减少文字量,降低作品定价,让农民买得起。如今改进文风成为重要课题,赵树理的浅易文风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范例。当下创作者应学习他摒弃故作高深的表达,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传递深刻思想,让作品更广泛地被大众接受。
当下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直播盛行,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说/听”的方式获取信息和娱乐,这与赵树理所处时代的大众文艺有相似之处。当下创作者应借鉴赵树理的经验,改变表达方式,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适应时代需求,推动大众文艺不断繁荣发展。
乡土中国之子赵树理
【主讲人:傅书华】
在中国新文学顶尖作家中,赵树理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对其研究的意义不应该完全局限在文学界,因而将他定义为“乡土中国之子”,较之称呼他为中国乡土作家要更为准确一些,这是超越文学范围的。
仅仅就文学创作而言,赵树理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范型,这种创作范型,拥有两个核心,一个是“问题”小说,一个是“中间”人物。
问题小说是什么呢?赵树理曾说,当自己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主题。很多人对赵树理的创作有误解,认为他是在配合政策而创作。比如他写《登记》,大家说是配合宣传《婚姻法》;比如他写《李有才板话》,是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写《地板》是为了辩清楚到底是土地更重要还是劳动更重要。很多人认为,赵树理的“问题”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他的“问题”应当是农民的利益被改变时所出现的问题,赵树理一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和进行创作的。
赵树理写的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中间人物。比如在《小二黑结婚》中,是在歌颂小二黑和小芹的新农民形象,但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三仙姑、二诸葛这两个中间人物;还有如《登记》,是在写农村艾艾和小晚这一对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但写得最成功的却是艾艾的母亲“小飞蛾”这个中间人物;1958年发表的《锻炼锻炼》,是在写青年干部杨小四,但写得最成功的是中间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饱”。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是谁?就是特别看重个体利益,有好处就跟你干,没有好处就想办法对抗你的普通农民形象,他写这种人物特别生动,也更为成功。
这样的中间人物为什么他写得很成功?因为他写的是乡土中国当中最真实的农民。文学从本质上讲应是“人”的文学,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整体化的人,而是鲜活的个人。五四运动时期在文学领域提出的“人的文学”,就是以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利益作为价值本位的。赵树理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农民,因此在他看来,只有被农民所接受、维护农民个体的利益并转化为乡土之上的民间伦理道德的文学,才能被农民所接受。
赵树理的小说是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符合老百姓的阅读趣味。比如《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结婚虽然受到阻挠,最后还是结了婚,老百姓都认可,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认可,二诸葛和三仙姑还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而现实中,故事的原型人物一个横遭身死,一个离乡远嫁,但赵树理却写成了大团圆,满足了老百姓追求圆满的朴素心理和愿望。当然还应当看到,赵树理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这种写法的核心在于要去书写发展中的现实。《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原型虽然是个悲剧,但是让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是符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的,所以他将这个悲剧通过创作变成喜剧。
赵树理的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描写乡土中国的民间心理。譬如,他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主人公“小腿疼”“吃不饱”在个人劳动与回报不能直接实现时,就想尽办法不出工,但如果当下干的活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两个人出工就比谁都早,积极性一下子就能起来。后来,有些学者把这部小说抬得很高,说只有赵树理敢于写出农民真实的愿望。但其实赵树理对“小腿疼”和“吃不饱”还是有所批判的,是从民间伦理出发,认为懒惰总是不好的。所以赵树理既写出了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从劳动到日常的物质生活的真实,也从民间伦理的角度对被集体化影响了个人日常生活的人物、行为,进行了批判,应该看到,赵树理的小说构成是很复杂的。
在今天,重新研究赵树理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现代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各种价值观念也随之而来,不但是我们和下一代人价值观念不一样,就是同代人在价值评判标准上,也经常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什么作为评价社会进步和评价现实生活的标准?赵树理根植于乡土,站稳人民立场,无疑在当今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的一生写了很多作品,包括大量的地方小戏,也包括秧歌、鼓词等,他并不在乎这些作品是否登得了大雅之堂,是否能让他在文坛有一席之地,他所看重的是老百姓是否真正接受和喜欢。赵树理的人民立场,赵树理所看重的传播形态、传播方式要适应一个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接受水准审美趣味,当然,这个接受水准审美趣味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在发展着的变动着的。所有这些,在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个真实的赵树理是什么样子,赵树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创作到底美在什么地方,我们只是站在一个角度阐述一个方面,阐述这个方面,就会忽视他另外的方面,但这也正好体现了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被人不断地阐释、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的。汪曾祺说“赵树理最可赞处,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好情趣”。在我看来,汪曾祺对赵树理的评价是最准确最到位的。
赵树理对当代乡土文学的启迪
【主讲人:葛水平】
20世纪60年代,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间,人们常常把山西省的一批小说作家称为“山西派”或“《火花》派”,这种以地区和所办刊物名称作为创作流派的命名,尽管是朴素的、直觉的,但却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这个流派的共同点,可以概括如下:
在题材上,都择取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汾水流域广大农村沸腾的生活,都带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和晋中盆地的气息。这些作家都是脚踩泥和农民一起摸爬滚打、血肉相连。赵树理当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在谈论自己和作品中人物的关系时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李有才板话》中老字辈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产的人。”
在表现形式上,都极其通俗化、群众化。这个流派的作家们都熟练地运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白描手法,运用人民群众中醇厚、质朴、生动、活泼的语言,不仅人物的对话,而且叙述语言都是口语化。他们吸收我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艺的长处,又加以创造,既无浮泛的堆砌,又无纤巧的雕琢。
他们都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锐利的笔触从生活的表层深入到生活的内核,在思想内容上敢于描写人民内部矛盾冲突,揭示在新旧社会交替的伟大时代里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不平凡的历程。
而用“山药蛋”来命名这一流派,主要是这一流派的作家大多来自山西农村,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山药蛋”是山西农村常见的农作物,代表着质朴、接地气的农村生活,用它来命名,体现了作家们关注农村、扎根农村的创作特点;另一方面,“山药蛋”平凡、普通但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特点,就像这些作家的作品,虽然描写的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琐事,但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性光辉,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赵树理出生在贫农家庭。这个家庭和他生长的农村环境,给赵树理带来了三件宝:
第一宝是他懂得农民的痛苦。他家原先种着十来亩地,但地上都带着笼头,就是说指地举债,到期本利不齐,债主就要拿地管业。从他出生到抗战开始的30年间,他的家和他自己是一直呻吟在高利债主重压下的。总而言之,他是穷人,他是穷人的儿子,他真正知道农民的艰难是什么,懂得农民的经济生活,知道农村各阶层的日子都是怎样过的。
第二宝是他熟悉农村各方面的知识、习惯、人情等等。赵树理自己上过学,放过牛驴,担过炭,拾过粪,跟着人家当社头祈过雨,参与过婚丧大事,总之是他在农村实顶实活了那么大,再加上他父亲遗给的那些“知识”,他就算得上是真正熟悉农村了。
第三宝是他通晓农民的艺术,特别是关于音乐、戏剧这一方面的。他参加农民的“八音会”,锣鼓笙笛没一样弄不响;戏台上的乐器,他件件可以顶一手;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把戏就能自己耍。
他同时又是多才多艺的,能写字下棋,还会画几笔山水画,也能刻图章。还能耍把戏,讲笑话,只要他一在场,管保男女老少通夜不散。他能够接近群众,不只是他的感情和群众一致,也不只是他懂得群众最多,这些艺能也实在帮助他不少。
赵树理谈创作,特别强调“读者意识”,“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类似的话,赵树理多次说过。
先确定读者,再确定写法。实际上也就是读者决定着写法。这样,在叙述语言上,也就会最大限度地接近农村中初通文墨者,甚至是完全不通文墨者的理解能力、接受水平。在《也算经验》一文中,赵树理把这种语言追求说得更具体。农民听不惯“然而”,就写成“可是”;“所以”让农民陌生,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
能用最省俭的语言,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不存半分模糊,这种本领绝非轻易能够练就,更不是每个作家都能练就。由于赵树理是以巨大的美学意义上的才华去追求“老妪能解”,其叙述语言也就仍然有着一种赵树理式的神韵。
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小说创作的两个基本方面。要让大众读者喜爱、要让农村中的识字人和并不识字的普通农民感兴趣,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却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大众读者、农村中的初通文墨者和普通农民,他们听评书、看演戏、读小说,是要看与自己熟悉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是要欣赏日常生活中没有的故事、人物、情感。换言之,他们喜爱的“文艺”,必须具有强烈的通俗性。而通俗性的典型表现,是传奇性。传奇性是通俗文艺最基本的属性。
赵树理的叙事方式正是民间艺人的叙事,他用说书人的方式去叙述故事,还进一步糅合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叙事方式,刻意迎合了民众的审美趣味,将一件件琐碎的故事娓娓道来,层层铺展得自然而生动。他的作品往往注重故事性,让故事围绕人物逐层展开,且为了兼顾趣味性,还会设置一些悬念。赵树理擅长用朴素无华的口语,并不刻意去追求方言土语。但他也不做过多心理活动的语言描述,因此不是孤立地对人物性格做专门的刻画。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李婷婷
本版图片:本报记者史晓波
本版责编:赵欢 版式/制图:刘铁军 王静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